因冬虫夏草改变的命运

生长在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的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菌的寄主——蝙蝠蛾幼虫

刚挖出土的冬虫夏草
文章转载自:《中国科学报》 (2017-12-08 第4版 自然)
因为它懂得合作与节制,这个物种才得以延续。如果有一天它消失殆尽,那么损失的绝不仅仅是这一类物种本身。
■本报记者 胡珉琦
2015年,在江西南昌发现了目前国内结构最完整、布局最清晰、保存最完好的汉代列侯墓园——海昏侯墓。当时那里出土了上万件珍贵文物,创下多个“考古之最”。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发现,一盒保存了2000多年的冬虫夏草。也许早在西汉时期,虫草就有可能已经成为了名贵滋补药材。这也意味着中国采集冬虫夏草的历史延续了至少2000年。
冬虫夏草素有“黄金草”之称,仅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区域内的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以及与我国接壤的尼泊尔、不丹、印度等国喜马拉雅山系高寒草甸内,其他地区和国家均无冬虫夏草分布。可受到这些年掠夺式采挖的影响,冬虫夏草野生资源日益匮乏。
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冬虫夏草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他生物存在复杂的共生关系。因为它懂得合作与节制,这个物种才得以延续。如果有一天它消失殆尽,那么损失的绝不仅仅是这一类物种本身。
最成功的演化策略
药用冬虫夏草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清朝汪昂的《本草备要》(1694)。他不但指出了冬虫夏草的功效“甘平,保肺益肾,止血化痰,己劳咳”,而且描述了这一物种最具特点的生活史,“冬在土中,形如老蚕,有毛能动,至夏则毛出土上,连身俱化为草。若不取,至冬复化为虫”。
尽管中国人利用冬虫夏草的历史至少长达2000多年,但这种民间认识始终藏有谜团,谁也说不清这个“冬天为虫,夏天为草”的过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直到最近40年里,中国的科学家才一步一步揭开这个物种特别的演化故事。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杨大荣就是最早对冬虫夏草连续进行野外科考的科学家之一。
“冬虫夏草的地下部分的确是虫,但地上部分却不是草而是真菌的子实体,而且一旦成为冬虫夏草就永远不会再变为虫。”身为云南人的杨大荣,自从1978年第一次挖到冬虫夏草,就没有间断过对它的好奇和研究。
每年的夏天,青藏高原有一类昆虫蝙蝠蛾会从卵孵化成幼虫,它们除了短暂的3至7天的成虫期外,一辈子都生活在地下,而这也是它们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因为它们正好会遇上冬虫夏草菌子囊孢子成熟后弹落入土。一旦被冬虫夏草菌所感染,菌丝就会钻进幼虫体内,吸收它的营养,直至把它“杀死”变成僵虫。越过冬天,冰雪消融时,虫草菌不断生长,不久后一根棒状的“草”就会从僵虫的头顶长出地面,这就是冬虫夏草菌的子实体。
对蝙蝠蛾来说,虫草菌就像“鬼魅的幽灵”,被附体以后便吞噬了它原本的灵魂。但大自然的精妙就在于,表面上看是一场“侵略战”,其实却是一次恰到好处的合作。
虫草菌对感染蝙蝠蛾幼虫是相当有节制的。杨大荣提到,这个比例在自然界虫草分布区大概是12%。也就是说,大部分蝙蝠蛾幼虫仍可以继续繁衍生息。尽管,目前科学家并不清楚具体的感染机制。
而且,如果没有虫草菌的感染,对蝙蝠蛾也未必是件好事。分布在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的蝙蝠蛾主要以蓼科、禾本科等植物的根芽为食,偶尔也取食少量木本植物的嫩根,如果没有天敌,幼虫大量生长繁殖,会很快消耗掉它们所拥有的食物,致使蝙蝠蛾无法生存。因此,虫草菌和蝙蝠蛾、蝙蝠蛾和高寒草甸植物之间,维持着一个可持续的平衡状态。
有意思的是,杨大荣发现,虫草生长数量多的地方,往往活着的蝙蝠蛾幼虫也更多。这就给出了一个重要讯息,如果冬虫夏草被耗尽,那么我们失去的很可能不是一种虫草,我们还会失去非常古老的蝙蝠蛾科昆虫。
杨大荣介绍说,凭借这种共生关系而存在的虫草在全世界有多达400多种,在中国就有100多种,但是,冬虫夏草是仅限于青藏高原所特有的一个种,所以人们也称它为“中华虫草菌”和“中国的国菌”。它的特别就在于它采取了一种很成功的策略,也就是对青藏高原分布的蝙蝠蛾是唯一的寄主昆虫,不像其他多种虫草可以把许多种群昆虫当作寄主。虫草菌对高原蝙蝠蛾情有独钟,在杨大荣看来,高原蝙蝠蛾科的昆虫绝对称得上是整个青藏高原的优势物种。
目前中国已知的蝙蝠蛾科昆虫,绝大部分种属都分布在青藏高原,共6属46种,其中可以作为冬虫夏草寄主昆虫的就有37种。而这些昆虫的分布中心,恰恰就是现在冬虫夏草的主要产地。
蝙蝠蛾非常古老,它起源于白垩纪中后期,当时,南亚次大陆上的原始蝙蝠蛾因为板块漂移和碰撞,才到了青藏高原地区。随着高原不断变化、隆升,自然区域有了显著的隔离、分异。在新的环境中,蝙蝠蛾经过变异、遗传,不仅成为了高山高原草甸和草原的占领者,也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种群。
实验中,杨大荣就发现,四川、云南的虫草菌感染西藏蝙蝠蛾的效率很低,就算有的成功感染,最后也长不出“草”来。这也意味着,在漫长的岁月里,虫草菌和每一种蝙蝠蛾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精细的协同进化关系。
半人工培植
冬虫夏草之所以受到如此追捧,不仅仅是它存在方式的奇特,最重要的还是它被赋予的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关于冬虫夏草的记录,它通常用来治疗背痛、阳痿、黄疸病以及体虚,还有治疗肺结核、哮喘、支气管炎、肺气肿等。除此之外,很多人相信,冬虫夏草具有抗肿瘤的效果。
杨大荣解释,这是因为过去它被认为含大量具有抗癌、抗菌活性的虫草素。可就在今年,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最新证实,冬虫夏草中根本没有虫草素合成基因。事实上,就冬虫夏草抗肿瘤和治疗其他多种疾病,到底是什么活性物质起作用,至今也一直未知。
不过,他同时也表示,药典记录的功效,以及民间用它提升免疫力,尤其是加快术后恢复,目前在临床上还是给予肯定的。只不过,冬虫夏草对应各种功效的具体成分,在医学上始终没有找到确切答案。
在杨大荣看来,虫草的“神奇”还是大有炒作的成分。但市场从来就偏爱炒作,目前质量最差、几乎没有药效的空瘪和破碎的冬虫夏草的价格是8万元/公斤;质量一般的在12万~16万元/公斤;质量中等的是18万~30万元/公斤;最贵的则可以达到60万元/公斤。
由于冬虫夏草的稀缺性,上个世纪80年代,杨大荣一边在野外研究冬虫夏草的形成机制,一边也开始进行人工繁育的尝试。但是,仅仅是研究和养活这些寄主昆虫,他就花费了二三十年时间。
蝙蝠蛾出色的高海拔生态适应性,对人工繁殖来说,是最大的阻碍。在高寒、高紫外线、稀薄空气的高海拔地带,一般一只幼虫需要最少蜕6次皮,海拔高的需要蜕皮8至9次才会进入预蛹和蛹期,3年左右才能完成一个世代,海拔高的地区差不多5年才完成一代。如何模拟它们的生存环境,让它们适应低海拔的实验环境,实现规模化繁殖,是科学家攻克的重点。
可问题又随之而来。杨大荣表示,尽管目前寄主昆虫的规模饲养已经不是难题,但经虫草菌感染后,真正能够长成子实体的效率非常低。如果这一步骤无法突破,冬虫夏草人工培养就称不上成功。
不过,现在科学家并没有将视线主要集中在实验室环境的人工培养技术,他们更希望冬虫夏草有一天可以实现半人工培植。杨大荣就在香格里拉的研究基地与当地的一些牧民家庭进行合作,主要方法是把人工养殖的蝙蝠蛾幼虫和人工培养的虫草菌放归到自然环境中,增加寄主昆虫的种源和菌源,然后仍然依靠当地的虫草菌感染。另一方面,他每年也会定期去产区进行宣传,指导人们科学管理和采挖冬虫夏草。
事实上,这样的合作关系更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一损俱损
由于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整个青藏高原雪线上升,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的冬虫夏草分布格局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杨大荣发现,冬虫夏草主产区内核心分布带已经明显变小,30年前冬虫夏草核心分布海拔地带在3800至4500米之间,而目前核心分布海拔上升到了4400至4700米之间。原来冬虫夏草分布较集中的海拔4200至4500米地带,种群数量也在逐年减少,有部分地带已经多年没有长出冬虫夏草,也没有发现寄主昆虫了。
更重要的是,在巨大利益的带动下,“淘金者”们疯狂采集这一物种资源,导致其数量锐减。杨大荣给出的数据显示,如今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冬虫夏草的采挖面积扩大了5~6倍,但总体产量却和过去相当,甚至还有所减少,大概在50~80吨。也就是说,单位面积的产量已经下降很多。即使有些是当年冬虫夏草生长最密集的地方,科学家采集到的虫草条数、发现的寄主昆虫都寥寥无几。
青藏高原有“亚洲水塔”之称,而虫草核心分布地带就处于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源头的高寒草甸,其生态地位在整个亚洲都举足轻重。
试想,在一个春夏之交,一个青海地区就有20万人投入“淘金”大军。一座山头,一天之内,可能经受上千人的踩踏、挖掘,采集者在草原生火,留下生活垃圾,这些都会造成严重的生态恶果。
杨大荣说,过去每年虫草采挖季节结束后,草山上都会留下无数坑洞。这些坑洞不仅将寸草不生,还会不断沙化,可能引起整片草原的退化、沙化。他曾在20年前挖掘虫草的地方调查发现,草皮至今都没有恢复。
在青藏高原,冬虫夏草除了和生态环境存在密切的关联,也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
整个冬虫夏草的产地生活了2000多万人口,在民族志纪录片《冬虫夏草》中,青海当地的牧民对着镜头表示,如果没有虫草,他们不仅盖不起房,诸如农药、化肥、种子的购买,收割机械的租用等等都只能付诸空谈。随着虫草价格的上涨,一人采挖一斤虫草就能抵得上三年打工收入。虫草经济收益与其他收入来源的巨大差距,是推动很多牧民采挖虫草的动力。
但虫草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很多受雇佣的劳动力进入采集区后,“神山”的神圣性也受到挑战,那里出现了被挖过的土坑。有的草场主因为收取数百万草皮费而一夜暴富,放弃自己的牛、羊。他们有能力在县城买房,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同时,也有人赚了钱在酒吧、赌场挥霍,互相攀比,甚至吸引了大量乞丐,当地每年因虫草产生的纠纷不计其数,衍生出了不少治安问题。民风民俗的变化,同样也是杨大荣在青藏高原40年调查行走的真实感受。
在这个过程中,虫草采挖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经历了一些变化。现在在西藏、青海的重要产区,当地多个部门会联合组成执法队,严格限制采集的地区、人数、时间等等,目的是杜绝乱采滥挖。杨大荣表示,科学的采集管理政策对资源保护还是有效的。
不过,任何脱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保护都是片面的。当大量的科学研究都在关心如何人工种植冬虫夏草时,不能忽略虫草对当地老百姓的意义。冬虫夏草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种保护与延续的问题,也是如何与当地百姓共存与发展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就是自然界本身,虫草菌和蝙蝠蛾百万年协同进化的过程就是最好的示范。虫草资源、当地百姓、科学家、管理者也应该成为默契的合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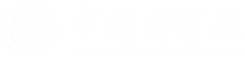

 青公网安备 63010402000197号
青公网安备 63010402000197号